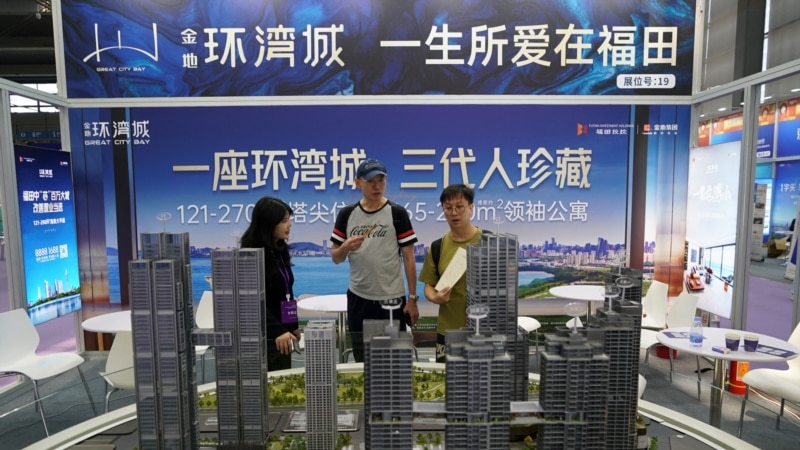九年前上任的加拿大總理賈斯汀·杜魯道的倒台最終來得無聲無息。在補選失利、民調數字下滑以及最終以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克里斯蒂亞·弗里蘭於12月突然辭職為高潮的黨內不安氣氛中,杜魯道曾多次堅稱他打算參加下一屆聯邦大選。但在1月6日,他在渥太華的一次情緒低落的新聞發布會上,結束了他的假期隱居,確認了幾周以來似乎愈來愈不可避免的事情:辭職,並暫停議會至3月底,讓自由黨選擇繼任者。
杜魯道的倒台與其崛起時的炫目氛圍形成了鮮明對比。2015年,他在加拿大自由黨經歷了四年來最糟糕的選舉結果後復甦該黨,其全國知名度迅速轉化為閃閃發光的國際品牌。年輕、上鏡且病毒性,杜魯道的勝利成為全球轟動,點擊誘餌商人為他的外貌、瑜伽姿勢和五顏六色的襪子而讚嘆不已,並且大西洋兩岸的報紙都興奮地加冕他為新的進步標桿。自2008年奧巴馬當選以來,西方領導人從未獲得如此熱烈和不加批判的接待。
然而,從這些伊卡洛斯般的高峰,這位自由主義的救世主最終將以一個極不受歡迎和不被喜愛的人物離開政壇。他的支持率甚至低於喬·拜登,而自由黨在全國民調中僅徘徊在微不足道的16%(相比2015年接近40%的支持率)。如果今天舉行選舉,保守黨將以壓倒性優勢獲勝。
是什麼原因造成如此巨大的命運逆轉?一種看法廣泛存在於媒體中,似乎也為一些自由黨議員所持,即杜魯道政府這些年“過於左傾”,因此失去了神話般的中間地帶,這被認為是所有政治成功的基礎。
除了其他事情外,這是一種完全忽略政府在其受歡迎程度和成功的巔峰時期形象的解釋。回顧2015年加拿大和國外的頭條新聞,你很容易會誤以為杜魯道的勝利是某種地震般的現象,類似於富蘭克林·羅斯福1936年的大勝或克萊門特·阿特利1945年的勝利。儘管他有著精英背景和相當傳統的中間派綱領,杜魯道被廣泛描繪成一位左翼民粹主義者,其即將上任的政府將代表“現代史上最具雄心的自由主義首相之一”。在2015年競選期間和之後,杜魯道本人非常願意傾向於這種形象:承諾投入數十億美元進行他所謂的“加拿大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要求國家中“最富有的人多繳稅,以便我們的中產階級少繳稅”;並承諾合法化大麻和改革加拿大的簡單多數選舉制度。競選口號“真正的改變”可能(故意)模糊不清,但對於數百萬選民來說,它意味著對氣候變遷、經濟再分配和激進政府的積極行動。
不論是誠心還是故意,杜魯道以改革者的身份參選並獲勝。自那以來,他和他的政府變得極不受歡迎,這與他們拋棄中間地帶的關係不大,而是他們試圖固守的教條式願望的反映。如果仔細閱讀細則,杜魯道主義從來就顯而易見地是一個維護現狀的項目。儘管有一些真正的進步政策——尤其是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的新福利、一個仍在萌芽階段的國家托兒計劃,和與社會民主黨達成議會協議的一系列讓步——他的政治計劃的大部分動畫精神主要是中間派和技術官僚;其目標和目標比變革性更具表面性。
在賈斯汀·杜魯道身上,加拿大選擇了一位完美適合2010年代社交媒體時代的總理:一位上鏡、貴族氣質的領導者,其根本上傳統的風格被一種焦點測試的改革雄心和進步提升信息巧妙地隱藏起來。在對第一次選舉勝利一週年給出的一個特別(即使是無意中)揭示的評論中,杜魯道本人這樣描述他的政府成就:“我們能夠在大家普遍傾向於關閉的時候與歐洲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我們能夠在每個人都希望保護環境的時候批准(新石油)管道。我們能夠表明我們理解人們的恐懼,並且有建設性的方法來緩解它們——而不僅僅是踢體系一腳。”
與這一模式保持一致,杜魯道政府在一系列問題上——從土著和解到氣候變遷,再到大型雜貨連鎖店的住房和價格欺詐——的進步姿態往往更多是言辭上的而非實質上的。就像杜魯道自己被各種腐敗醜聞和2019年他過去塗黑臉的揭露所磨損的空氣形象一樣,政府的受歡迎程度已經減弱。在執政九年後,自由黨偏好假裝解決社會不公而不是真正解決它,越來越難以讓選民接受,他們支付著高昂的租金並排隊在創紀錄的食物銀行。
政府因其現已被罷免的領導人左傾而注定失敗的敘事將對某些人來說是方便的,也可能會被幾位尋求繼任的候選人——包括弗里蘭、前英格蘭銀行行長馬克·卡尼,外交部長梅拉妮·喬利,和前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省長克里斯蒂·克拉克——所接受。
但在最終評估中,杜魯道主義的衰落故事不太像是一個關於進步揮霍危險的警示故事,而更像是一個關於21世紀中間派自由主義的弱點和不足的警告。事實證明,“消除人們的恐懼”是一個無法替代追求真正結構性變革的麻煩且更具爭議性事務——這一點可能很快會被加拿大右翼力量採用,並帶來毀滅性後果。
(内文照片来自GOOGLE)